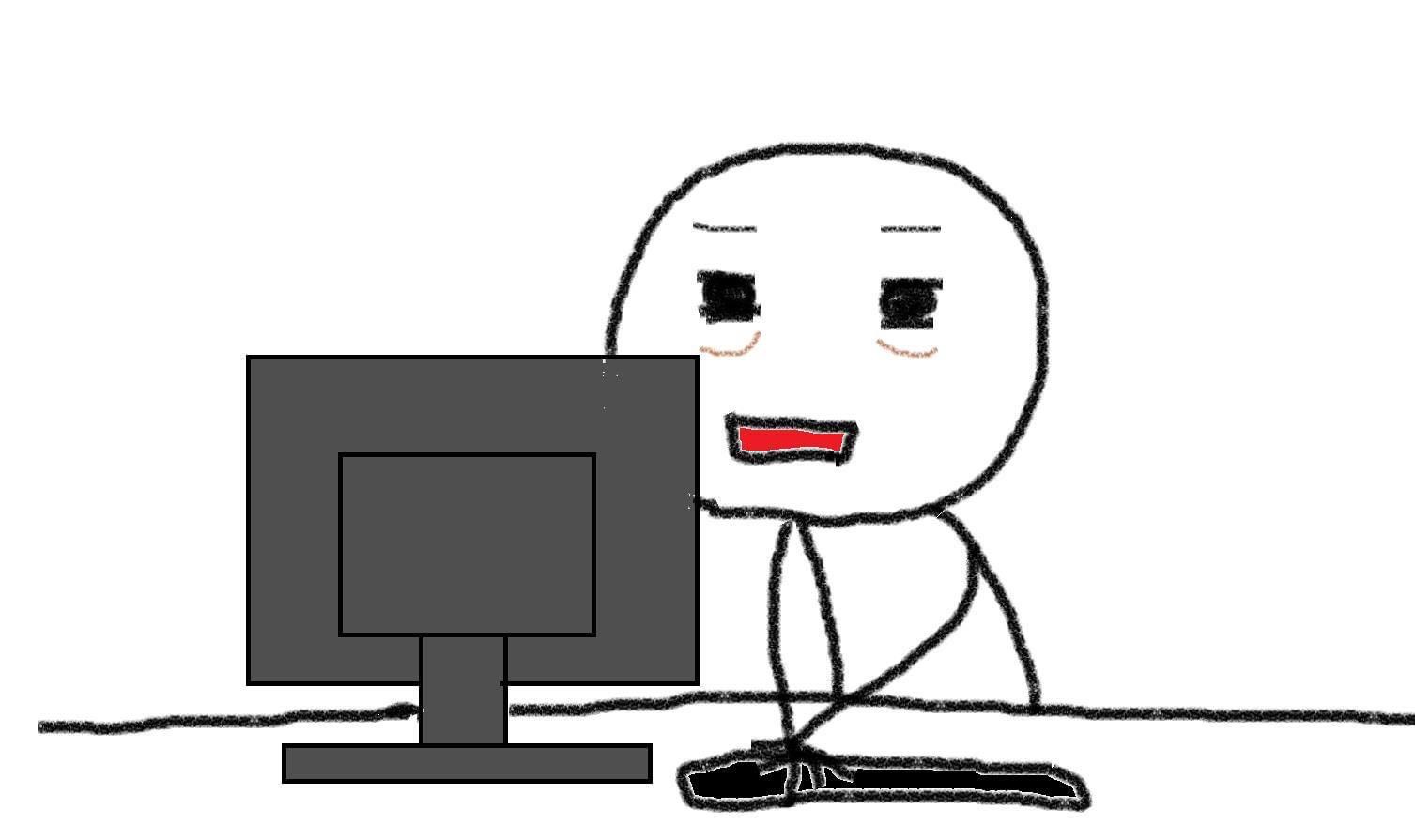1. 滾落縫底的戒指(一)
窄小的樓道,老舊斑駁的牆面。
底樓加蓋的鐵皮屋在炙熱的夏天裡,總是讓人有一種在悶鍋裡被蒸煮的窒息感。
他們家裡太窮了,窮到一貧如洗,冷氣是他從小到大都沒看過的高科技產品。
僅有的只有一臺母親從回收場撿來的,勉強堪用的老舊電扇,在悶熱的夜晚中,用盡全身的力氣,吱嘎吱嘎的轉動著,即使那麼拚命,卻也起不了任何降溫的效果。
他躲在碗櫥裡,窄小黑暗,甚至還有蟑螂爬過,他已經習以為常。
碗櫥的拉門已經生鏽變形,關都關不牢。
他蜷縮著幼小的身體塞在角落,冷冷地透過縫隙看著外頭的景色。
那是母親瘦小的背影,孤零零的被拖來拖去,不時發出淒厲的慘叫與哭聲。
粗暴的野獸又喝得醉醺醺,在寂靜的夜晚用他那瘸了的、不好使的雙腳拖沓著,爬上那窄小的樓道,砰的推開那扇一點用處都沒有的木製門板,見著母親就抓起來左搖右晃,使勁地打,不論母親如何喊叫求饒也沒有用。
他已經習慣那種場景,在這樣的夜晚,野獸的腳步聲踏上第一階時,母親就會立刻將他抓起來,塞進碗櫃,告訴他千萬別出聲,然後用瘦弱的身軀承受著這一切。
待到外面動靜漸歇,他知道,這一切都結束了。
他得趁野獸心滿意足的昏睡過去,起身放熱水澡讓母親清洗身體,拿出藥膏,幫母親處理傷口,一如他以往做的那些。
都習慣了。
習慣了。
習慣……
……
真他媽的,這種事情怎麼可能習慣呢?
林峴濰猛然從床上彈起,狠狠的抹了一把臉,這一覺睡得十分不安生。
多久沒夢見的場景,竟然趁他精神脆弱之際入侵。
他待在床上喘了口氣,想要驅逐夢中那種憤怒與無力感,然而漸漸平復後,興起的卻是另一段不堪的回憶。
他馬的。
他看著被自己壓得刺痛的右手掌,那裡縫了10來針,是昨天跟蘇昶起爭執時,他情緒一時失控,順手拿起花瓶往牆上砸,破碎的玻璃片在他手掌割出了一大口子,讓他在深夜獨自壓著血流不止的手,招了車往急診室去。
然而讓他沮喪的不是這件事情,而是當他將他倆搬來這間房子同居時,一起挑的那只,有紀念意義的花瓶朝蘇昶扔時,蘇昶那臉上的表情。
是的,他竟然使用暴力,用他最不屑的方式溝通,最終他的身體中流淌著的還是那個男人的血,野獸的血,暴力的基因。
林峴濰想,他搞砸一切了,待花瓶碎裂一地時,他忽然意識到,他倆的關係也跟花瓶一樣回不去了。
儘管他的手不停的滴了滿地的血,也不能阻止男人離去的失望背影。
到底是什麼時候開始,他倆之間再也沒有任何溫情,每天見面就是爭吵、嫌棄?
林峴濰恍惚的下床,像是想起了什麼,渾渾噩噩的打開了酒櫃旁的一個置物櫃小抽屜。
最上層的那個抽屜,通常是他得到的各種名片,有用與沒用他都隨手扔進那兒,堆得都成一座小山了他也沒在乎過,是啊,反正找不到蘇昶會幫他找……
林峴濰從來沒認真看過這些名片,他胡亂的揮著名片堆,好不容易從中找到了一張純白的名片,上頭是一個心理治療所的心理師聯繫方式。
這是某年,蘇昶在他酒後大哭時,遞給他的一張名片。
「我覺得你需要去看醫生,需要專業的幫助,你的父親給你帶來的陰影太大,幾乎覆蓋了你整個人生。」
但是酒醒後的林峴濰並不以為意,他覺得他好得很,他現在長大了,父親也早就死了,那種垃圾,怎麼可能會給他帶來什麼影響呢?
然而事實證明,蘇昶說的話總是比他有道理、有智慧。
他的確需要,他一直無法從他父親給他帶來的童年陰影中解脫,最終他跟他父親一樣,是個會用暴力來解決問題的人。
他撿起了名片,輕輕關上抽屜,這時,眼角餘光瞄到櫃子下有一點閃光。
他彎身下去,趴在地上,在櫃子底的縫隙中,找到了一枚金戒指。
那是他與蘇昶的定情戒,當時他還不怎麼有錢,拚死拚活打工賺到了第一筆薪水的研究所窮學生,就將這筆薪水去銀樓打了一只金戒指,還因為錢不夠,這婚戒薄得不行,甚至都有點變形了。
即使如此,蘇昶還是非常高興,這戒指他從來不離身,洗澡做家事一律都戴著,就這樣他套牢了他10多年。在昨天的爭吵中,他扔了花瓶,而蘇昶,一臉漠然地拔了這枚戒指朝他扔了過來。
林峴濰抖著手,小心翼翼的將這枚戒指揣進胸前口袋中。
那是他心裡最柔軟的一段感情,他珍而重之地交到了蘇昶的手上,就在昨天,蘇昶將他的這份真心還了回來,他後悔了,他想挽回這段關係,希望一切都還來得及。
※
白無垢的牆面,木質的扶手椅以及稍嫌單薄的粗糙地毯,他緊張的摳著大拇指。
每當他焦慮、不安或是有任何負面情緒時,總是不斷這個動作,甚至嚴重到他有時候回過神來,滿手的鮮血。
坐在對面的心理師瞇著眼,溫和的笑了下:「您好,我是陳○○心理師,您可以稱呼我任何讓您感到自在的稱呼。」
林峴濰直勾勾的望著心理師手中的筆記本與筆,大腦快速飛轉。
心理師是一位年近五十的婦女,稍顯花白的頭髮在後腦勺紮了個馬尾,他想,這筆會在筆記本上寫些什麼?寫他是個噁心的野獸嗎?或是是個卑劣、脾氣暴躁的社會扭曲人格?
想著想著,林峴濰緩慢開口,他聽見自己且嘶啞的聲音在狹小的診間響起:「……那我就叫您醫師好了。」
心理師點點頭,隨即又溫和的開口:「那麼到這裡來想討論些什麼呢?生涯規劃?感情?工作?還是──」
「我是個同性戀。」
林峴濰打斷了心理師的詢問,他望著那對彷彿能看透自己的眼睛,他心虛了,害怕極了。
他從對方眼睛的倒影中看到了陰沉的自己,像是在那黑色的眼珠中旋轉,一點點地跟他那噁心的、可惡與惡劣的父親融為一體。
不自覺的,他忽然就像到豆子一般,想要將噁心不堪的、骯髒的自己全部傾訴給眼前的人,讓對方一邊掛著他那屬於心理師的虛偽的職業面容下,參雜著對他的憐憫與厭惡……
他一貫看到的,他人聽見他的過往後露出的神情。
他打了一通電話,詢問作設計的朋友,珍而重之的將那枚撿起的金戒指交給了對方。
同時述說了他的想法,希望對方將那戒指融合,加上其他新的素材,變成一枚新的帶有設計質感的戒指。
以前他窮,給不起一枚像樣的戒指,但是現在他有錢了,他是一個部門的小主管,背負著一些業績,有不少績效獎金,別說一枚戒指,就算是一枚大鑽戒都不為過。
在戒指製造的這段期間內,他惶惶不安,望著月曆上的日期,離蘇昶離開的那天,也過去快要半個月了,他一次都不敢聯絡蘇昶,他害怕蘇昶將他拉黑、封鎖。
然而他知道心底深處他最害怕面對的是,蘇昶不要他了。
他焦慮的等待戒指,越是晚一天,他越是害怕當他掏出戒指給蘇昶的那天,蘇昶的身邊已經有了人。
蘇昶是那麼的完美,不同於他一個技術人員,蘇昶是留英歸國的碩士,頂尖的一流公司執行長。而他只是一個大學畢業的小公司部門主管。
蘇昶英俊、溫柔,不焦不躁,不像他是一個砲管,對啦,就是砲管。
學生時期他就像個砲仗,一點就燃,周遭都叫他小砲管,說他脾氣壞,長相又普通,因此沒什麼朋友,第一個主動靠過來的,是蘇昶。
「今天說說你與蘇昶認識的經過?」
經過兩三次的諮商,林峴濰已經比較能夠適應跟心理師對話的過程。
雖然依舊憤怒、不安,甚至時常哽咽大哭到他自己都覺得丟臉。
但現在他已經比較能夠平靜地述說自己心裡那個壓緊的盒子中,深藏的祕密。
林峴濰輕晃著頭,回想著他與蘇昶的相識過程。
「我脾氣很差,老是陰沉著臉,上了大學後一個朋友都交不到。喔,反正我也沒準備交朋友。」
那時候林峴濰完全想跟所有人拉開距離,他害怕他暴躁的脾氣,時不時發作會像他父親那個野獸一樣,彈跳起來毆打別人。
那是一個初夏的午後。
他一個人從圖書館借了本書,坐在圖書館前林蔭下的長椅,藉著溫暖的午後陽光灑落的光線,一字一句的讀著。
這時,一個人就莫名地在他身邊的空位坐了下來,林峴濰無意識地往旁挪了挪,他想可能是哪個要暫時休息的人吧!
「你在看什麼?《快樂的科學》?尼采的書?」
林峴濰猛然抬頭,被灑落的陽光刺了下眼。
只見蘇昶微笑看著他,紅唇齒白,拉出一抹燦笑,單眼皮上挑的鳳眼笑瞇成一條線,隨即睜開,帶著好奇看著他手中的書。
「……念理組的竟然會讀這樣艱深的哲學書。」
「……」林峴濰有點被嚇到,他認得蘇昶,學校公認的校草,與他這個沒人緣的隱形人不一樣,是無時無刻被眾人簇擁著的風雲人物。
這樣的人怎麼認識他?還忽然跟他搭話了?
林峴濰緩慢的合起書,他想裝作沒聽見,悄悄的溜走,他可一點兒也不想跟人家聊起哲學什麼的。
「林峴濰,別跑,跟你說話呢。」
蘇昶一把抓住他的衣角,林峴濰登時漲紅了臉,竟然連自己的名字都知道。
這下可好了,他一屁股又給扯了回去,要是對別人他馬上發揮他的小炮仗個性,劈頭就怒吼起來,讓對發離他遠遠的,拉開一段安全距離。
可是這次他看著蘇昶那好看的臉,不知道怎麼了,竟是手足無措,完全失去了回應的本能。
「我、我……我就是想看看,這些哲學家不都想自殺嘛……」
林峴濰撇過頭,眼睛胡亂飄移,就是不敢正眼對著蘇昶那張臉,下意識結結巴巴的解釋起來。
他也莫名為何自己就這麼老實的交代了。
「喔?你好奇這個?那有研究出來嗎?」蘇昶又笑了,露出他的一口白牙。
林峴濰痴痴地看著他的笑臉,那一瞬間,他竟然墜入了愛河。
……
「所以?」心理師又刷刷地在他筆記本上寫了幾個字,林峴濰想看,但又沒膽子看。
對於心理師的問題他只是低下頭,靜默不語。
所以?所以那天他還是跑掉了。他看尼采、看康德,也看歌德的書,他想研究這些詩人作家哲學家腦子裡都裝了些什麼?是不是有人會跟他一樣?深受心裡那頭時不時出來作祟的野獸所苦。
沒想到蘇昶竟然問他為何要看尼采?知道了原因又怎樣?
「……所以我第一次知道我不是無法戀愛,而是我是個同性戀。」
良久,林峴濰聽見自己輕聲說。
蘇昶真的很溫柔,那次見面後,他時常在圖書館前的長椅上遇到蘇昶。
一開始他質疑過對方是刻意等待他,但他馬上又否定這項猜測。
不可能,他不起眼又卑劣,說不定對方就是想看他出醜呢。
結果沒想到蘇昶還真的是來等待他,他似乎摸透了林峴濰的課表,每當林峴濰的空堂,他便會露出那抹林峴濰難以招架的微笑,坐在長椅上等待他。
偶爾聊聊毛姆,或是聊著《少年維特的煩惱》中舉槍自盡的維特,最後聊到天體的運行。
無所不談,蘇昶是多麼讓人如此驚艷,如此博學多聞。
有時候林峴濰聊到興致高昂,忘了在他人面前作矜持,揮舞著手,在炎熱夏天的炙熱曝曬下,渾然忘我的高談闊論了一番蘇格拉底的哲學時,待他回神,卻看到蘇昶笑吟吟的托著下巴,專注地看著他。
那一笑就彎成月牙的眼,無時無刻就像落在水中的月彎那麼的亮。
他可真好看。
結束了這次的諮商,林峴濰在櫃檯領了藥,他已經吃了一個禮拜的抗憂鬱藥物,他覺得他好像比較快樂了一點。喔,快樂嗎?他不知道,以前和蘇昶在一起的快樂嗎?他想了半天,站在診所門口忽然覺得很茫然。
對了,他竟然忘記了,忘了現在的蘇昶面貌。
他們總是在爭執,蘇昶總是冷冰冰的看著歇斯底里的自己。
好久沒看到他的笑容了,是什麼時候忘記了那種最初的戀愛?
那時候,他分明是那麼的喜歡他……
林峴濰忽然感到胸口一陣揪痛,想見他,好想好想見他……
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★☆
我來了啊啊啊(默默看著隔壁斷更的外星喵)。
我是冬天才能過活的生物,五月連載完小花後,天氣一天一天炎熱起來,加上我換工作了之類的。
即使想振作將外星喵寫完,發現我腦子一片空白。
冬天時我會自己一個人出門在公園運動、購物,在樹下發呆一個下午打文章。
但夏天,尤其是連續好幾個禮拜38度的高溫,我根本非必要不出門,自然也無法好好發想文章。
結果只噴出許多腦洞,乾脆集合成一個小作品集中地。
至於《外星喵》,可能9月以後我就復活了吧,到時候再戰。
希望大家喜歡《小樹洞》系列會陸續補上一些腦洞,也許好看也許不好看,就,感謝大家捧場。
啾咪~~